临汾新闻网讯 核心提示:自闭症近年发病率在全球呈急剧上升趋势。中国残疾人普查报告数据显示:自闭症发病率已占国内各类精神残疾首位,目前,平均100个孩子中就有1个患自闭症。但是,患儿经过早期诊断、治疗和特殊教育,一部分能够获得较好生活质量,走入主流社会。因此,早期干预和训练至关重要。
上苍赐予人类一双慧耳,使我们能够倾听自然的声音,倾听美妙的音乐,倾听亲人、同伴的温暖话语……使我们每个人,都在倾听中成长。上苍还赐予了人类一个睿智的大脑,让我们能够理智地思考,冷静地看待世界,在聪慧中成长。与他们相比。显然,我们都是幸运的。

老师一遍遍教孩子们读书识字。
20双黑亮的眼睛,看上去与别的孩子的眼睛没什么区别。可只有静静地凝望上好一会儿,你才能发现,他们眼睛里倒映的是一个外人无法走入的世界。
这是一群折翼的天使。一个12岁情绪有些躁动的女孩似乎在看你,她的嘴角甚至浮起了微笑,还做出了拥抱你的姿势,可她扑过来只是死死抓住了你的胳膊狠狠咬上一口。
一个9岁半男孩的目光快速地掠过人,然后停留在自己的手上,他把两个大拇指抵来抵去,他比较着相同的指甲,膝盖、鞋子,然后是桌上相同的饭碗、相同颜色的积木。事实上,他在找事情干。
一个男孩,像黑暗的使者,头上始终戴着帽子,教室不起眼的角落里永远是他的归属,让他停留在大家视线的办法是,老师一直牵着他的手,即使如此,他也会悄悄溜回属于他的那个个体,静静地就那么待着,享受着只属于他的世界。
唯一热情的男孩,用无辜的大眼睛打量身边的每一个人,一只手托起下巴不停地问着,你是谁,叫什么名字?回答完他的问题,过一会儿工夫,他嘴角上扬,你是谁,叫什么名字? 空洞的眼神,怪异的行为,封闭的心灵,社会边缘化的弱势群体。因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他们被称作“星星的孩子”。
日前,记者来到临汾市洪洞县康乐康复中心,与这些“星星的孩子”进行了一次零距离接触,感受孩子的孤独,感动于家长的坚持,感受康复中心老师那份博大无私的爱。
一
第一次见到9岁的彤彤时,她有些羞涩,老师为她梳了一个朝天辫,看到有人,偷偷瞄一眼又快速地转过脑袋。和记者渐渐熟悉起来后,她又迫不及待地扯扯你的衣角,兴奋地咿咿呀呀向你展示今天的学习成果。
开朗、活泼,彤彤就像任何一个同龄的孩子一样好动、淘气。而坐在旁边的父亲一边注视着女儿,一边向记者“翻译”着女儿的话,眼神中流露着疼惜和欣慰:“(她读了这所学校后)变化很大。你刚才听她讲洗衣服、扫地、擦桌子(都会了),等于有个小帮手了。现在她在家里信心增长得比较快,原来见到家人都不肯交流,现在好很多。我觉得他们老师也用了很多心思去教,我觉得他们(老师)很棒。”
自2015年张虎的康复中心成立以来,无助的家长带着他们同样无助的孩子,从四面八方赶来。一个14岁男孩,父母亲都是硕士毕业,当孩子还在摇篮里的时候,他们就读着蒙氏教育的书籍,想把孩子培养成科学家,但医生却说,这是个“终身不能痊愈的自闭症孩子”。

老师的“小帮手”。
根本没有人能说明病因是什么,也没有完善的治疗办法。自闭症,这种“广泛性发育障碍”,就像恶魔一样,每20分钟就伸出魔爪,从地球上抓走一个孩子,不分种族、民族、家长的受教育程度。
从第一例自闭症患者——美国男孩唐纳德于1943年被确诊开始,自闭症已经进入人们生活的半个多世纪。目前,英国的自闭症发生率最高,87个人中就有一个;美国97个人中有一个;日本是112人中有一个。其他国家从1‰~10‰各不相同。各国的统计数据有较大差异,主要原因在于诊断的能力。国际社会普遍认同,全球自闭症平均发生率占人口总量的4‰。
我国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调查数据。但按照4‰这个比例数据来推算,我国的自闭症患者约有560万人。
很多家长是第一次从医生那里听到这个名词。他们最初几乎想象不到,这个医学简称只有“ASD”3个字母的病症,将怎样吞噬一个孩子,甚至一个家庭。
从小,彤彤就不愿意被人抱,一抱她就哭,拿手往外推人。她几乎不笑,眼神活泛,却很少与人对视。
彤彤冷漠极了。她不认识妈妈,不认识家,无数次走丢。妈妈找到她时,抱着她哭,她跟没事儿人一样,冷漠地推开妈妈。妈妈做饭,切了手,流着血,烫着了,她都不会多看妈妈一眼,就像陌生人。
快4岁了,彤彤还不会说一个字。她行为刻板、重复。喜欢撕纸,每天不停地撕。
这个古怪的孩子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穷的麻烦。她上幼儿园第三天就被退回来。
在康复中心像彤彤这样的孩子已经算幸运了,这里的绝大部分孩子,还不会说话,即使有语言,也很混乱,像来自火星的孩子。有的孩子能说话,却是鹦鹉学舌,不懂语言技巧。家长说:问阿姨好。孩子说:问阿姨好。哪怕最终花几个月他学会了:“我叫天天!”可他仍然不能理解“天天是谁”“我是谁”,更不能理解镜子里的人就是自己。
“这些太难了,他们的思维就像一条直线,只有一个方向!”康复中心的徐老师说。
他们对某些声音格外敏感。有的享受塑料袋揉搓的声音,有的喜欢听两个瓶子撞击声。有的一听到汽车自动锁门“嗤”地一响,就躁动不安。
他们动作反复、怪异。吃饭时,有的孩子吃一口青菜吐出来,用手捏捏,再喂到嘴里,不停地反复这个动作。他们喜欢玩手,可以一整天,让大拇指和中指揉搓,仿佛永远有搓不完的泥条儿。他们回家永远走一条路,家里的东西,只能按原样摆放,稍有改变,就会哭闹。他们有的像时钟、像导航系统一样,走到某个地方、在某个时间点、准点尖叫。
“自闭症患者的每个脑区功能各搞各的,之间缺少协调联系,正常人的大脑演奏的是和谐的交响乐,而他们的大脑就像即兴演奏的爵士音乐。”一名研究专家说。
而张虎和康复中心的其他老师们,努力让这场爵士音乐听起来更像人们熟悉的交响乐。
二
为了更好地帮助孩子们开口说话,康复中心的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张大嘴巴附带表情,一次次地反复发音。
这些并不专业、却实用的办法,有的孩子在训练几个月后,非常想发出“妈妈”这个词,可喉咙耸动、嘴角撇来撇去,就是发不出声,孩子、老师的泪水都在眼眶打转儿。所有人都等待着那个时刻,终于,孩子发出来人生的第一个词:“妈……妈。”
“喔,这实在是个好日子。”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会感慨。

欢乐的活动课。
琪琪是4月份来到康复中心的。起初,她扯着衣角,蜷缩在教室一角,人一靠近就尖叫大哭。
在康复中心,老师手牵着手引导她。让跳操、翻跟头,不停地体能训练,使她忙乱地没有时间玩手。为了改变她狂躁的情绪,老师每天选择一时段与她聊上一会儿天。
目前还很难说,琪琪会在这样的训练中最终变成什么样子。不过,2个月下来,琪琪康复得算是不错。以前从不说话的她现在见到陌生人会主动打招呼。
对于大多数老师而言,或许桃李满天下、学生功成名就就是最大的幸福。但康复中心负责人张虎无不感慨地说,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,无论是多么微小的变化都能给老师们带来莫大的宽慰和成就感。
“你要把这些个头很高的孩子也看成是三岁以内的孩子。你面对三岁以下的孩子,他刚学会走路还不会走,你要鼓励他起来再走。你不要希望他一下子会背乘法口诀、加法口诀,只要看到孩子有一点点进步,会喊爸爸妈妈,你就很高兴。”
尽管老师们并不奢望自己的学生有多么瞩目的成绩,但能让这些孩子融入社会、自食其力是他们最大的愿望。
三
走进教室里,一张张颜色鲜艳的图画和孩子们的笑颜,所传递的是绵绵的爱和责任。而在康乐康复中心,老师们正是用这份热爱与责任,让这些“折翼的天使”重新展翅翱翔。
鹏鹏是一名典型的自闭症儿童,6岁了还不会说话。刚到康复中心的时候,他总是一个人独处,不合群,喜欢蹲在地上抠泥土,或站在高处斜着眼睛瞟着这个与他无关的世界,与其他小朋友的行动总是背道而驰。鹏鹏的情绪很不稳定,他会忽然间没原由地嚎啕大哭起来,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,有时甚至哭得筋疲力尽才罢休;然而,瞬间他又大笑起来,情绪问题严重影响到他的学习生活。鹏鹏的妈妈放弃工作陪着他,从他2岁半就开始踏上求医求学之路,三十几岁的年纪已经是满头白发;爸爸则为家庭的生计而每日奔波着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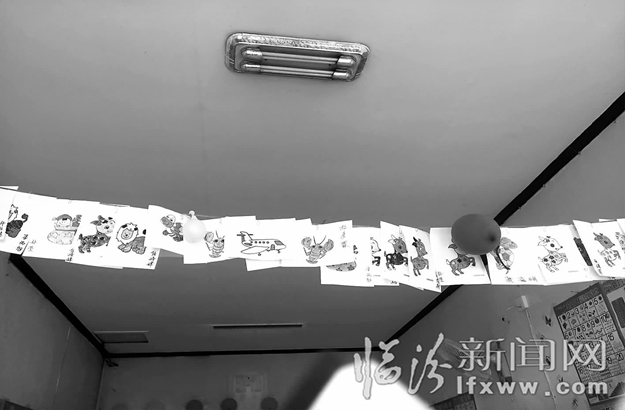
每一幅精彩的作品都蕴含了老师和孩子的极大努力。
“我们家里所有的人不怕苦、不怕累,只是每时每刻都希望奇迹出现,希望鹏鹏有一天能开口说话,能叫一声爸爸妈妈,能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游戏,我们就知足了!”
看着鹏鹏,康复中心的负责人张虎老师心里也很难过,他决心用爱心和专业知识引领鹏鹏走出孤独的世界。为此,老师们根据鹏鹏的实际情况为他制订出了个性化教育计划,在日常教学和生活中一点一点地矫正、引领,并施以认知、感统、语言等多种训练。同时,做好家校配合,家庭和学校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。老师们用心呵护鹏鹏,营造了一个温馨、安全的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,帮助其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状态。
在实际教学中,老师发现鹏鹏的模仿力很强,于是就从这个优势入手,发展他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,以优势带动劣势,取得了突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艰苦努力,鹏鹏取得了很大进步,这让所有的人都备受鼓舞。在2016年母亲节时,鹏鹏向妈妈说出了“我爱妈妈”这句久违的话。鹏鹏的妈妈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,禁不住泪如雨下,这一刻她已经等了6年了。在场的父亲也感动得泪流满面。
虽然鹏鹏的进步很大,但这只是“万里长征第一步”,自闭症康复训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星星的孩子要走出孤独,路很长。
乐乐刚来康复中心的时候,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咬人,他咬遍了所有的老师和几乎所有的小朋友。另外,他还经常趴在地上,用舌头舔地、舔墙,还喜欢把舌头从嘴里拉出来,自己玩舌头。
经过几天的接触,徐老师发现,乐乐咬人是孩子很少出门,胆子很小,加上他对外界不信任,所以咬人只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。
由于乐乐经常咬人,其他孩子的家长要求把他清除出去。但是,徐老师们觉得不能把乐乐推向社会,否则将贻误孩子的一生。于是,徐老师主动承担起看护、训练乐乐的工作,眼睛时刻不离,有异常举动就及时制止,并训练他听指令。开始的时候,乐乐中午不睡觉,徐老师就抱着他,用手轻轻拍他的后背,经过很长时间,才养成了乐乐睡午觉的习惯。徐老师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。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,乐乐很少咬人了,也不玩舌头了,舔地、舔墙的行为也没有了。
乐乐非常聪明,走上正轨以后进步神速,这让徐老师颇有几分得意。在准备2017年“六一”儿童节演出时,乐乐排练节目演得特别好,徐老师认为这下小乐乐肯定要出大风头了。然而,儿童节那天乐乐还是怯场了,她故态重萌,一下子坐在地上不起来,节目也演砸了。
当然,徐老师并没有责备乐乐的意思,她是觉得自己没有把这一情况考虑周全,没能让乐乐表现出最优秀的一面而感到有些自责。“在对自闭症孩子的教学中,有很多突发情况,再有经验的老师也会措手不及,因此,特教老师需要多方考虑、持续学习,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患儿服务。”徐老师反思道。
牛牛也是一个典型的自闭症患儿,刚到康复中心的时候,5岁的他就像一个大号的婴儿,吃饭、喝水需要喂,睡觉也得有人抱着,情绪非常不稳,经常无理由地大哭大笑,而且极易受环境影响:别人哭他也跟着哭,听到老师批评别的孩子他也会哭。不高兴了还会使劲揪老师头发,咬自己的手臂。主管牛牛的李老师对此也很“头大”。
“第一节个训课牛牛是在哭声中度过的。”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,李老师给他喂水、喂饭、抱着牛牛睡觉,逐渐建立了一点信任。牛牛喜欢听音乐,五音不全的李老师开始给牛牛唱歌,虽然唱的基本上都不在调上,但是这种“原创”的音乐还是引起了牛牛的注意。突破口找到了,老师与牛牛的对话也因此变成了“唱话”,对牛牛的训练也渐有起色。
今年四月,春暖花开的季节,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。越来越多的人说牛牛变了:自己吃饭了,自己喝水了,自己睡觉了,小朋友哭他能不受影响,学会些许自控了,课堂上也能静坐了,做错事能接受批评了(仅限李老师,其他老师说他还是会哭)……
也是在四月的一天中午,李老师接到牛牛妈妈打来的电话,因家里有事,放学不能接小牛牛了,刚好李老师顺路,问可不可以帮忙把他送回去。“我硬着头皮接下重任。要知道我只是在学校带他,还从来没在校外带过他呢!他会跟我走吗?”李老师说自己当时很心虚。怀着期待与忐忑的心情盼到了放学。没想到,牛牛乖乖地跟着李老师,牵着她的手一步步往家走。“如果有人跟在后面,你会发现我的脚印都在笑!”至今想起来李老师还是难掩激动,“谢谢牛牛,终于让我走进了你的世界!”
四
社会公众对待自闭症儿童的态度和意识,也是攸关他们康复的关键环节。
康复中心负责人张虎讲,一位妈妈带着自闭症患儿在公园玩耍,旁边一个老太太喊自己的孙子:“你别跟他玩儿,他是傻子!”这位妈妈非常愤怒,感觉受到了侮辱,从此,即使是别人多看她孩子两眼,她也会对人家怒目而视。
“在公交车上,孩子出现异常行为后,人们异样甚至鄙视的目光就像一束束飞过来的钢针一样。”所以,很多家长都宁愿把孩子放在家中,也不让他们出门,怕出去后遭到别人的“围观”。
其实,自闭症的孩子需要走出去,认识外面的世界,多与人接触,锻炼沟通能力。如果总是闷在家里,很可能会加重自我封闭的程度。
这就需要社会公众能对自闭症孩子的异常行为多一份包容,多一份理解,少一些惊怪,少一些围观。对于家长来说,也要调整心态,不要因为少数人的不良行为而耽误孩子的康复。家长还要克服虚荣、要面子、不敢见人、自卑等心态,要坦然面对,积极行动。
所以,自闭症孩子的康复需要更多的支持,除了经济援助、政策扶持之外,还需要精神的支持、感情的慰藉。“哪怕是一个微笑、一个鼓励的眼神,也是对自闭症孩子莫大的鼓励,愿人人都做引领他们走出自我封闭世界的天使!”

展示孩子们笑靥的照片墙。
康复中心的徐老师给记者讲了另外一件事:一天她打电话给一个送馒头的,要10块钱的馒头。
“你是哪里?”
“我是康复中心,你知道吗?”
“知道,不就是傻子学校嘛!”
徐老师听了很不高兴,但没有发作,等送馒头的来后,与他讨论。卖馒头的也很不好意思,他说自己是无心的,表示以后再也不这样说了。
这说明,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还是对残疾人有一些成见,尊重、帮助残疾人的社会意识需要整体提高。
“社会是多元的,残疾人也是社会的一分子,我们应该平等对待他们。他们又是弱势群体,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和关爱,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。”
是啊,自闭症孩子的康复是一个系统工程,需要社会的全方位支持。如果人人都能献出一份爱心,那么这源源不断的爱心将为自闭症儿童的康复铺就一条光明大道,“爱心接力融化孤独”的目标就能实现。(文中所有患儿均为化名) 记者 李娇 文/图
编后 尽管自闭症一词创立已经上百年,但人们对其认知还停留在“性格内向”阶段。我们应该加大宣传力度,让更多人关爱、了解并帮助这些“星星的孩子”,让孩子们感受到来自全社会对他们的关爱。愿人人都能献出一份爱心,让“来自星星的他们”健康快乐地成长。

责任编辑:张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