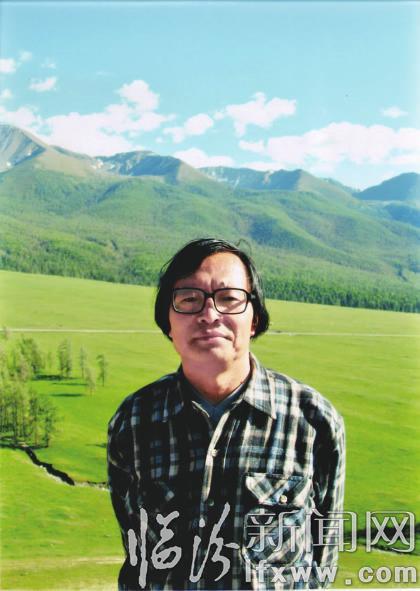
临汾新闻网讯 拨开一帘细雨,正是春日平阳。
在我市日益活跃的文学领域,可寻到这样一股清风,他在诗词书海里面享受恣意人生,在流年日深里笔耕不辍,他胸中有大义,心里有文学,提笔写故事,落笔既华章。
痴迷文字,藏书万册有余,他就是张行健——我市作家协会主席。
思考大于创作
1983年的秋天,张行健在汾河岸边一把火把自己创作的一百多首诗付之一炬,那些诗饱含着他对诗歌的热爱,还有他的青春梦想。那年,张行健25岁,就读于山西教育学院中文系。
“不能烧、不能烧!”张行健叫来给自己告别诗歌作见证的同学不以为他真的如此决绝,但他想的很明白:“有诗人的激情,没有对诗歌的掌控,对诗歌的理解不到位,思维和自由诗不合拍。”虽然每每读起顾城、北岛和舒婷的诗,总是能让张行健心潮澎湃,可他认为,做诗不是一件能凑合的事情,既然自己不适合做诗,还是罢了。
与诗歌告别,张行健没有一丝犹疑。
“大学期间,我接触到省作家协会一些作家,他们思想前卫,对我触动很大,特别是李锐,让我对创作有了新的思考。”张行健对于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,在李锐办公室,他用蹩脚的普通话背诵《静静的顿河》,这是俄罗斯文坛上不朽的巨作。李锐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居然对此有所涉略,他站起来给张行健递了一杯茶,“以后我们以兄弟相称吧。”这杯茶是对张行健的认可。
那个午后,张行健和李锐谈俄罗斯文学、谈诗歌,李锐对张行健刮目相看,推荐他读李泽厚的《美学》,这部书塑造了张行健对文学的认识。“小说不是简单的写一个故事,散文也不仅是要表达自己的情感,这部书让我对文学创作有了广阔的视野,作家创作如果不解决视野问题,创作便不会长远。”张行健十分庆幸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比较早。
1984年,张行健的处女作《秋风萧瑟》在《山西文学》第七期发表,这在学校引起不小的轰动。此后,张行健在文学的王国里自由探索。他的作品先后被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作品与争鸣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散文选刊》《读者》《中国文学》(英文版)(法文版)转载和翻译,入选《山西建国五十周年优秀小说选》。先后获得“人民文学优秀散文奖”“山西文学优秀小说奖”“路遥青年文学奖”“第二届赵树理文学奖”“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”“山西首届优秀签约作家奖”“娘子关优秀作家奖”。
散文《婆娘们》获1990年——1994年《人民文学》优秀散文奖、山西电台首届全国文学作品大奖赛一等奖,短篇小说《山校》获1989年——1993年《山西文学》优秀小说奖。
至今,张行健已著有长篇小说《天地之约》《古塬苍茫》《心魔》共三部,其中《古塬苍茫》入选《山西百年长篇小说史纲》。中短篇小说散文集已出版《天边有颗老太阳》《秋日的田野》《黑月亮》《在故里的上空飞翔》《倾听生命》《北方的庄稼汉》《激情乡野》《祖槐寻根》等10部。发表中篇小说30余部、短篇小说50余篇,共500多万字。
谈起文学创作,张行健对于很多年前看到的一首诗难以忘怀。“文学,你应当成为揭露黑暗的探照灯……文学,你应当成为广大人民大众追求光明的翅膀、歌颂爱情的唢呐。”在张行健看来,这首诗把文学的功能写的既透彻又全面,“文学就是写人物内心隐秘之处的欢乐和痛苦,写人物的生存状态。”如今,张行健对于文学创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,他认为创作分为三个状态:兴趣之爱、职业之爱和灵魂之爱。即便写作生涯的履历如此辉煌,他依然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停留在第二个阶段,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他持有敬畏,也将用毕生精力去靠近。“真正的文学精品可流传百世,思考越深远,创作境界才能越高。”
童年生活是他创作的源泉
不难发现,张行健的作品很多都是反映农村风貌、具有地方文化特色,小说里的人物似乎就在我们身边,因为真挚,才能触动人心,这和张行健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。
张行健出生在物质和文化都贫瘠的年代,故乡县底镇翟村在当时是一个有5000人的村子。村西是梯田,土地成片,庄稼长势喜人。村东是沟梁坡堥,农户家和庄稼地往往相隔五六里,每年的收成上交公粮后剩不下多少,在张行健的记忆里,自己在22岁前一直都是半饥半饱的状态。“如果小时候能吃饱,我肯定还能长高点,长到一米八我就不搞文学 了,去打篮球。”张行健打趣道。“以前,我们一年放三个假,麦假、秋假和年假,放假就是干活,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过。”从小便切身感受到农民生活的困苦,这些记忆深深印刻在张行健的脑海中,也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素材。
上小学的时候,张行健最害怕村里开大会,一开会学生就要列队参加,张行健就低着头,听别人批斗自己的爷爷,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,张行健的性格愈发内向压抑。“内向的人成年之后总要找一条宣泄情感的渠道,我选择了文学,通过文学表达自己积累的情感,再上升到对生命的体验。小时候的我,因内向便把兴趣寄托在阅读上。”小姑姑家的一个木箱子是张行健的最爱,那是父亲珍藏的一箱子书。张行健的父亲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,在当时因家庭成分原因,仅留存的一些书也只能寄存在小姑姑家。“箱子里的书有古典文学、中外小说,还有四大名著,我现在收藏的一套《红楼梦》就是当年父亲箱子里的那套。”小时候,每每拿出箱子里的书,张行健都会如饥似渴的阅读。
童年时期阅读,还有另外一个途径:交换。
“你知道赵树理吗?我有一本赵树理的小说,你呢,有什么小说?”“我最近手头没有,我给你两本小人书吧。”拿到同学分享给自己的赵树理的小说,张行健如获至宝。“不到两千字的小说,情节特别好,有层次感,形象鲜明。三个人物代表三个阶层,反应农村真实生活,当时对我触动特别大。”张行健便有意学习小说中的写作手法。
当时和同学交换书属于“地下活动”,因为阅读这些书是不被老师允许的,但这丝毫不影响张行健阅读的热情,《青春之歌》《柳青的创业史》《山菊花》……能拿到手的书,张行健都会一字一句去阅读,并且乐在其中。后来,张行健升入初中,语文老师郝老师会给学生吃“偏饭”,用刻蜡版印一些课外读物,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《保卫延安》……至今,张行健都能背诵出这些文章,“越是贫瘠的年代,对文学作品感受越是深刻。”在他看来,那是他最早的文学启蒙。
文学创作需要传承
为了发现青年人才,培养文学界新生力量,繁荣我市文学事业,张行健在主编的《平阳文艺》和《晋南作家》这两个刊物上不断推出文学新秀,为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提供广阔的平台,并多次组织笔会,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创作机会和环境。
2014年元月,我市作家协会签约了十名青年作家。在市一级签约作家,我市在全省是第一家。“一个特别可爱的老头。”这是签约作家荀莉眼中的张行健,“除了崇拜还是崇拜,张主席十分爱才、惜才,他不停地鼓励我们创作再创作。”打开荀莉的微信朋友圈,除了分享与文学有关的文章,就是自己随兴创作的诗句。
“张主席不遗余力帮助我们,他会组织各种采风和培训,用他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创作时如何处理人物关系、如何构架故事内容。”在签约作家梅子看来,张行健总是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提升创作水平,“请知名作家来临汾讲座,送我们出去学习,张主席如此用心,我们创作愈发有动力。”人之与文学也,犹玉之与琢磨也。
信手拈来、操翰成章绝非一蹴而就,那是很多个日夜张行健挑灯耕耘的积累。
记者荀丹薇

责任编辑:付基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