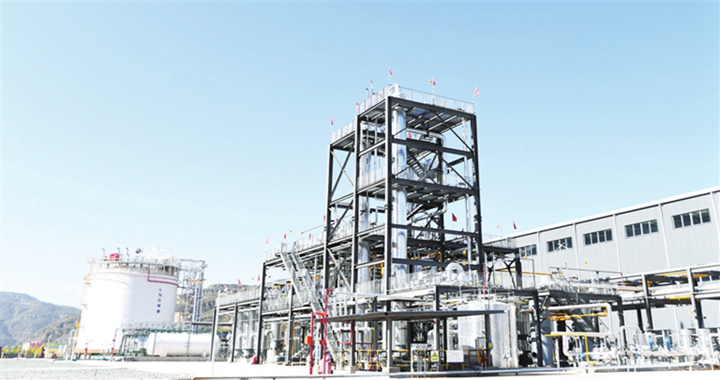临汾新闻网讯“买根麻花吃得香、咬得脆,买个刀子还不贵……”11月17日,在蒲县黑龙关镇传统古会上,打铁艺人范海鸿幽默的介绍吸引着老乡驻足。在他面前的摊位上摆放着上百件镢头、锄头、斧子、镰刀等常用农具,每每有人询问、购买,他总会自豪地说上一句,“都是我自己打的,放心用!”
常言说世间有三苦:打铁、撑船、卖豆腐。打铁,历来被人们认为是最苦的行当之一。49岁的范海鸿出生于蒲县克城镇克城村,由于家境贫寒,13岁时便开始跟随姥爷学打铁。“由于年龄小、力气小,抡锤抡得胳膊都肿了,但是手中的活儿还是不能停下来……”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,每次干完活吃饭手根本不听使唤。无数个日夜的辛勤汗水炼就了范海鸿的打铁技艺,19岁时他终于可以出师了。但,姥爷认为范海鸿是个打铁的苗子,便给他找了一位老师。“如果说打铁苦,那种莫名其妙的刁难,以及心里的煎熬才更苦。”一年的学艺生涯让他暗下决心,“不蒸馍馍争口气,我一定要活出个样来!”
姥爷看在眼里、急在心里,思前想后找了自己的同门师兄弟来教导外孙。打铁是一门配合度较高的技术活和力气活,特别是打制锋利刀具之类的利器时尤其需要帮手配合。“记得有一次,师傅抡着一米多长、六七斤重的大锤锻打,不想锤子落偏,直接砸在了我的肩膀上,那一刻的疼痛是刺心的。但我们这行有个行规,一件物品没打成就不能离手,所以我只能忍痛坚持。”学艺的艰辛令范海鸿记忆犹新。
其实,范海鸿也曾有过放弃的念头。“师傅爱讲笑话,每次看到我情绪低落时,他总会说笑话哄我开心,同时也会讲一些做人的道理,比如,在打铁时要做到‘低头是计、抬头是眼,不要小看那一点点边角料,它们可都是金子、银子,就看你会拈不会拈’……”这时候,受到开导和鼓舞的他又会“满血复活”。
3年后,范海鸿正式出师了。怀揣着两位恩师所教授的技术和人生道理,他靠着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“打扫的勤、拾掇的勤”的人生信条,积攒了人生第一桶金,并于22岁时自立门户,开始专心打铁。
日子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流逝。20世纪80年代,农业机械使用还不普及,铁制农具广泛使用,所以那时铁匠相当吃香。对于每一件铁制器具,范海鸿总是尽量做到精益求精。比如打好一把锋利的菜刀,从下料、烧铁、剖铁加钢铁,再到烧铁、融合、锻打、封口、刨光等,要历经十余次1100°C高温火炉、上万次铁锤锻打,任何一个细节他都不敢有丝毫马虎,因此他也很自信自己打制的菜刀的使用寿命和质量。
匠心换来认可。每天守着铁炉,看着狭小的打铁铺火花四射,听着烧红的铁具遇水哧哧作响,范海鸿凭着过硬的手艺,让家人过上了安稳的日子。顾客对他的手艺也分外钟情,十里八乡找他打铁的人络绎不绝。
然而,随着时代发展,曾经辉煌的古法打铁业举步维艰。迫于生计,范海鸿曾于2013年前往湖南等地打工,凭借过硬的焊铁技术,一度拿到了每月8000元的高薪。但仅仅坚持了一年,他便毅然决然地“打道回府”了。“就像写字一样,几天不写手都生呢,打铁更是。这门手艺是我辛辛苦苦学来的,是两位师傅毫无保留教会的,我舍不得撂下,也不想让这门老手艺在我的手中失传……”说到这里,眼前这个性格坚毅的中年男人哽咽了。闲暇时,他会在自家铺子前点根烟发发呆,“我这辈子就跟铁匠这行当一样,学艺时经历千辛万苦,壮年时到达顶峰,而后逐渐没落……”
好在范海鸿觉得有点盼头了。当看到越来越多的手工技艺获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,他说:“我会一直打下去,打进‘非遗’,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。”
记者 亢亚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