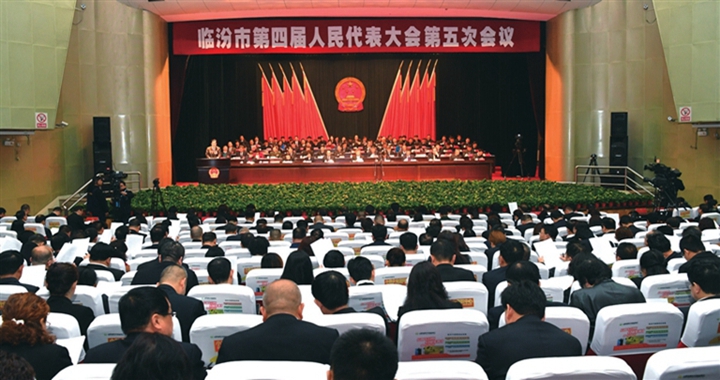难忘一方土
乔建仲
乡愁,就是你离开了一个地方,还会时不时惦念,时不时牵挂。
一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我们一群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响应号召,去隰县刁家峪乡羊头神村插队锻炼。羊头神村位于县城西南三十多公里,西接永和,南邻大宁,“鸡鸣闻三县,一脚踩三邑”是这里区位特征的生动写照。因位于黄土高原深处,天然的屏障,使这里历史上幸免于外族的侵扰和战争的践踏,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在此完整地保留与呈现。有别于水土流失的贫瘠土壤,羊头神村土地肥沃,大自然给予这里更多的青睐与恩惠。春夏之际,行走其间,天宏地阔,山幽泉香,微风习习,拂动一望无际的麦浪,让人心旷神怡,游目骋怀,醉心忘我。
或许由于没有使用农药的缘故,山间的野草上有许多颜色各异的小昆虫爬来飞去,多彩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,白天劳作或行走的路上会见到松鼠、野兔、褐马鸡等,偶尔还有从高秆作物里蹿出的狐狸,村子里的每一棵大树上几乎都有喜鹊、乌鸦做的窝,村民们常以它们的叫声来聆听亲朋好友到来的信息。
站在羊头神村向西眺望,“棋盘山”“石磨山”等依次排列,每座山都有属于它的美丽传说与故事。“棋盘山”上有一盘石棋,据传是神仙下过的,凡人去了以后,只能下却拿不走。不远处的山头,据说是北宋女将刘金定练兵时,因鞋子灌进了泥土,脱下鞋轻轻一磕,磕出了两个山头,后人称之为“双锁山”。
戎与祀乃古之大事,远离战争侵扰的当地人敬树如神,年久高大的树木常被奉为神灵予以祭拜,这种习俗曾延续很久。由于对树木的崇拜,一些区域禁止人们践踏、砍伐、放牧,在客观上使得山间的植被有一个生长喘息的机会,从而保护村庄生态的延续,生活的所需,农牧的持恒。
二
在羊头神村与农民一起摸爬滚打了整整三年,我对农民和农村的体悟非常深刻,即使在后来有十多年的乡镇工作经历,但也是对插队三年所感所得在认知上的充实、丰富和提升。
村民们做人的准则,处事的哲学,淳朴憨厚,静闲恬适。头上的毛巾,中式的裤子,黑布的老鞋,腰间的旱烟杆,一年四季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昼夜相继,虽至清苦,倒显自在。
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,春节这天,农民都要去田地燃放鞭炮与土地相伴过节,很多老农在桑榆暮景之时,都要去自家田地里走一走看一看摸一摸,对土地的无限眷恋和情深挚爱可见一斑。
插队三年,当时的劳动是由生产队长派工集体劳动,没有具体的劳动定额,田间歇息、阴雨天或冬闲时,村里的长者总是给我们讲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》及当地的神话传说,趣味悠长,印象深刻。在讲到《三国演义》时说,刘邦百年之后,在阴曹地府被韩信、彭越、臧荼三人拉着在阎王爷面前告状,三人指着刘邦说:“我们给你打下江山,你却把我们杀了”。阎王爷见状言道:“既然如此,你们转生人间,一人为一方王以诉你们的冤屈”。他们就是后来三国的曹操、刘备和孙权。这些故事显然是随着社会的变迁,几代人不断演绎流传下来的口头文学,后来我翻遍了《三国演义》等书籍也找不到这些故事,但不论如何演绎,其主题永远紧贴忠孝、仁爱、信义等传统文化精髓,以此来鞭策后辈做人行事。
三
耕作是农民世代坚守的千年生命接力。耕耘、耱耙、打藏样样精通,任何人都可以说是种田的行家里手。常言春雨贵如油,春天一旦有雨,农民会用耱的方式使土壤保墒,以备春耕播种。庄稼的种子是用饱满度来衡量优劣的,播种小麦前不仅要观察种子的饱满度,还要用手指插入种子中凭其温度来感知优劣,这使我第一次惊讶地发现,种子不但有生命,且这种生命是有温度的。
一年四季的农事依照二十四节气而行。为更好地便于记忆,指导农耕实践,当地人将长年累月观测星辰日月、风云物象的经验,用谚语进行总结归纳。“惊蛰十天没硬地”(指惊蛰10天左右大地解冻),“未到惊蛰雷先鸣,四十五天不见晴”(预示年景不好)。农作物的生长伴随着从春到秋的风雨阳光,这是自然的法则。春天和风细雨,大地回暖,利于幼苗生长。夏季雨水丰沛,阳光充足利于庄稼成熟。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随处可见,春天桃花、杏花、梨花等先次盛开,随着由春及秋的推进,风力也逐渐加码,将果树上残次的花朵“过滤”后,留存下优质的花朵,以确保秋季硕果累累。
除播种庄稼外,人们的外出远行也是通过对天象物候的观测来决定的,“蚂蚁搬家蛇过道,明日必有大雨到”“朝霞不出门,晚霞行千里”。天上出现勾勾云,日月晕环,刮南风或东南风等等都是下雨的先兆。
四
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丰富多彩的。男人以田间劳作为主,女人以操持家务为要。当时女人粗粮细做、绣纳缝补无所不能,全家一年四季的衣服鞋袜都由妇女包揽,每逢换季时,棉衣棉裤是对女人们制衣技巧的大比阅。
当时农民物质生活过得虽有些清苦,但精神生活却十分富足。就医而言,民间有许多传承下来的偏方。在田间劳作时手脚免不了划伤流血,遇此情况,当地人会用一种随地生长的刺棘草的汁液来止血防破伤风;在田间被蜂虫叮蜇,用抽旱烟的烟油涂在伤处可解除疼痛浮肿。
羊头神村于我而言,虽非故乡,却胜似故乡。我曾多次返乡探望,每次听到最酸楚的话就是:“老一茬人都走了。”的确,我是一个个听着、看着或送着他们走了的。我深知伴随他们而去的是一种文化,一种生活和生存方式。
出于对一方热土的深深眷恋,我相约几个同龄乡亲沿着冰封雪锁的山路和原野,把70年代的旧村跑了个遍,只见一孔孔土窑洞长年风蚀雨浸,大多已坍塌,不少农家院前茂密枯萎的杂草枝高叶蓬,随处可见的棘条已挡住我们的去路。只见老树下曾将多少粗粮野果磨碎的石磨老态孤单地蹲在那里,背倚墙脚历经岁月的陈箩旧筐随风摆动,仿佛在述说发黄的往事,那些祖传的陶罐瓦坛里装满了岁月的风声雨滴,依旧挂在墙上的那把老镢早已锈迹斑斑,全无当年锃光瓦亮的铁性。
农民节俭质朴,敦厚善良,倾其一生默默奉献,他们黧黑的面孔,堆起的皱纹,慈善的目光,粗糙的双手,满身的泥土,这铭心的记忆在我脑海里多年都挥之不去。他们勤劳勇敢,自强不息,用厚实的肩膀和不屈的脊梁把一个民族挺立了数千年。
斗转星移,光阴荏苒,伴随时代的变迁,扬弃发展的新生代农民,不少已入城居住,城市给予农人新的平台与天地,他们正用勤劳的双手打造未来,而羊头神这片热土赋予他们的优质品性非但未曾流逝,反而在新时代彰显出新的活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