祖先行迹里的人间正道
——评李琳之《祖先,祖先》
近年来,李琳之的图书一本一本相继摆上我的案几。《黄土魂》《感喟秋雨》《中华祖脉》《家国往事》,每一本到手我都认真阅读,爱不释手。如果要对他的散文归一个类型,我觉得多属于文化大散文。这么说,似乎有凑热闹之嫌。其实不然,李琳之是在声名鹊起的文化大散文沉寂后揭竿而起的。而且,他的文章一出手就不落俗套,无论是写作手法,还是所表现的思想,都是自我的、独到的。这就是我喜欢阅读的原因,阅读的一篇不敢落下,一句不敢跳过,唯恐错过了闪光的亮点。一个作家有了个色,无论外界如何评价,文坛都无法忽略他的应有席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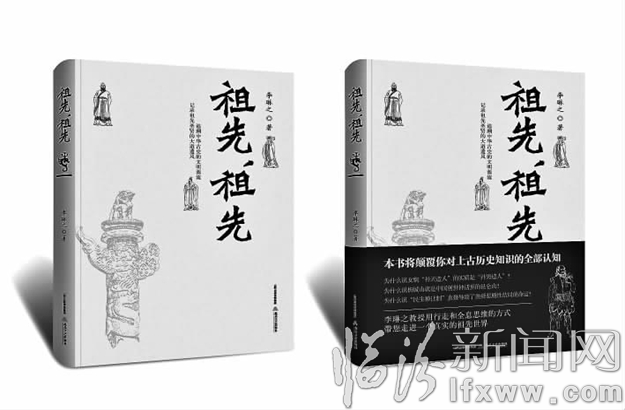
《祖先,祖先》,李琳之著,北岳文艺出版社,2017年6月第1版。
还沉迷于李琳之创设的文化散文氛围,他又发来了新著《祖先,祖先》。天下第一等好事莫过读书,何况先睹为快乎?小荷才露尖尖角,独占春色诵新篇,美哉,美哉!不过,这一次读得并不轻松,读得心里沉甸甸的。关键在于,这是一本探究之书,这是一本质疑之书,这是一本辨析之书,也是一本求真之书。该书的内容不算复杂,但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是一个作家的良知和担当。
国人喜欢炫耀伟大祖国历史悠久,文化灿烂。这毫无争议,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认识这悠久灿烂的资源。唐太宗李世民曾说,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这说法国人普遍认同。以此逻辑推论,我们祖国历史悠久,打开往事,就可以镜鉴兴衰,就可以明辨是非,老马识途,何况人乎?遗憾的是,我们常常前路迷茫,不知所从,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。内中原委是多方面的,但有一个致命的因素是通用的历史不是一面本真的镜子,而是一面哈哈镜,是一面扭曲了的镜子。就以李琳之笔下写到的炎帝、黄帝和蚩尤为例,在历史的教科书里蚩尤总是以反面人物的面目出现,黄帝则是正义的化身。真是这样吗?不一定,这是经过删削后的历史。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,大抵就是这个道理。黄帝胜利了,可以毫无顾忌地书写正史,可以把自己装扮得冠冕堂皇。而被肢解的失败者蚩尤只能被贬得荒唐恐怖,长得铜头铁额,三头六臂,这哪里还像人的模样?如此妖魔鬼怪,黄帝打败他、肢解他自然理所应当。但是,到了今天的山西运城历史上命定的解州,没有人读解州,平民百姓都众口一词地说是“害州”。为何说害?在他们眼里是黄帝把蚩尤害死了。一个“害”字可以看出对于蚩尤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。在当地民众眼里,蚩尤尽管失败了,但他是正义的,因为盐池原来就是他们部族的。黄帝抢占蚩尤部族的盐池,才引发了这场大战。
在晋南民间还流行这样的医疗词语:发炎和消炎。追寻词语的本意,还是起自炎帝和黄帝的那场大战。黄帝胜利了,下面的小部落并不服气,时常起事反叛,这就是发炎。黄帝赶紧派士卒镇压,这就是消炎。有一种说法,蚩尤原本是炎帝属下的一个部落,他和黄帝大战也可以视为发炎和消炎之列。我多说这些话,是为了强调一个观点,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,尽信书不如不读书。我非常兴奋地看到,李琳之对历史的追溯不仅没有拘泥于古人典籍里的成论,而且,十分注重对民间传说的搜集和辨析。据此,他才将位于山西阳城域内的析城山判定为古代的昆仑山,他才将中华文明的原点判定在析城山。我们对他的观点可以有不同见解,但是,他判定历史的方法却值得借鉴。更何况,他所做的判断是绝对不可忽略的一家之言。将蚩尤摆到与炎帝、黄帝同样的位置尊奉,不仅仅是个位置问题,还事关整个民族价值观、世界观。价值观、世界观摆正了,历史才不会成为哈哈镜。以史为鉴,才可能明鉴兴替,才不至于总在懵懂中摸着石头过河。
由此我深切地感悟到,该书最珍贵的不是他发现的那些观点,而是他考察探究历史的方法。昔年顾颉刚提出的“疑古论”,推动了考古实证历史的进程,却也产生了不应有的虚无论断,似乎还没有被考古证实的历史就难以成立。更为严重的是 忽视了传说,即口述历史。口述历史,虽然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难免误传,但是其中的蛛丝马迹恰是进入真实历史的幽径。况且,野史的真实程度往往不亚于正史。李琳之对口述历史的“大胆引用,谨慎求证”,恰是揭示上古文明的最好钥匙。
我对李琳之充满敬意,敬慕他的品格,敬慕他品格投射在纸卷上的作品。他的作品没有当今司空见惯的华丽外饰,有的只是真挚的倾诉。这似乎与新时期以来从西方克隆效仿的所谓新颖手法距离不小,也就缺少了新潮的奇异质地。不过,李琳之完全不必玩这种招数,他书写的人事和精神足以触及人心,自然不用玩弄外在的花活。却有一峰忽然长,需知不动是真山,他以我手写我心,而不是靠外在花样蛊惑世人。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粉饰。文字与史料浑然一体,与思想浑然一体,朴实无华,却意味无穷。为此,由衷地写下这点感慨,愿读者走进该书,去洞明新的天地。
(乔忠延)

责任编辑:张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