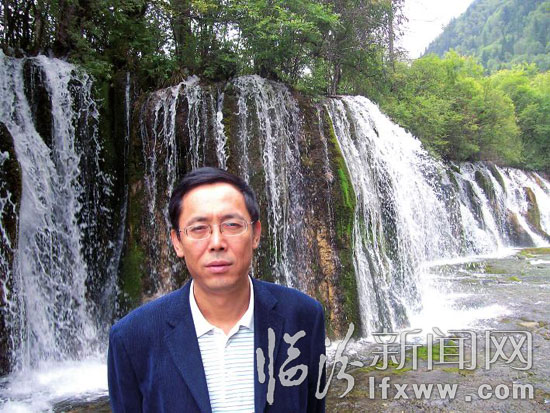
临汾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树德,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作的一批散文作品,在国内知名文学刊物发表后,引起专家和读者的首肯。著名文学评论家楼肇明先生在给高树德散文集《心事流亡》撰写的评论中认定,高树德的精神导师和艺术导师是沈从文。“我们认为他已确切无疑地行进在沈从文到刘亮程的文学航线上”。(楼肇明《困顿与位格—谈高树德散文集《心事流亡》)。高树德的文字摒弃滥情和媚俗。也许正是这种对文学追求的态度,近乎审慎,近乎神圣,十年时间,继《心事流亡》之后,第二本散文集《远行的村庄》才结集出版。从作品的数量上来看高树德的作品产量很低,品读高树德的作品,读者心里有种沉沉的感觉,这是否和作品的质有一定的关系呢?
面对滚滚红尘,作家还是要笃定地坐在冷板凳上。
就目前时代的变化,一个严肃的作家,持如何态度对待写作?就此,笔者请高树德谈了他的感知。
现代社会,随着城镇化的加快,国外发达国家花费200年时间完成了城镇化,中国仅用了不到30年时间完成了。沿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,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鸡犬相闻,春耕秋收,男婚女嫁,脑袋还停留在黄昏牧羊归圈浓郁气味的乡村,身子不由得被挟裹进高楼林立油炸食品飘荡弥漫的街道。城市化催生的新民众身心割裂,惊奇和失落并存,故园失却颓废,荒芜,欲望的新花园瓦砾灰渣尚存,速生的荒草和鲜花争夺这新民众的心理空间。全球化,我们原本遥不可及的天涯海角荒漠冰岛,交通运输业的高度发达,像似赋予了人缩地之法,黄白黑棕红生活的族群,像是村东村西的邻舍,东半球的狗吠,西半球的鸡也能听清,真是个小小寰球了。全球化使人们视野史无前例的扩大,却使人类的想象空间空前的缩小。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化,信息化是人类数千年未有之变。信息化彻底改变人类已有的生活方式和模式,作为作家不可能不受到其影响和改变。
便捷的信息传递,方便的输写工具。使这个时代的新民众,人人都可能成为发表作品的“写手”,人人都可以成为表达心声的“作家”。不必要依仗作家之手,不必要依赖作家的心智。无论是喜悦还是愤怒,他只要愿意,轻击键盘,就“OK”了。信息化给作家带来方便的同时,其压力也是明显的,要在恒河沙数的写手中突显出“这一个”不淹埋在群沙之下,比滚石上山还要艰难。国内一些著名作家也曾开了博客,经过一段时间纷纷关门谢客,知难而退可能是其主因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长篇小说,是年产1000余部,到了2011年上升到了3000余部。长篇小说年产量节节盘升,蔚为可观。这和信息便捷,写作提速,催生更多作家有关。但是,无论是1000余部,还是3000余部,推想既是专职读小说的评论家,不说在一年内读完了3000部,就是读完1000部也是相当困难。对一般读者来说念完几千部小说的名字也是个不小的工作。因而在产品如此丰饶的当下,能够叫大众记住的小说,能引起共鸣的作品屈指可数。不能否认无论是1000还是3000,平庸和优异并存,不能责备作家,更不能责备辛劳的作家,在网络盛行,并一直盛行下去的未来,分流读者已是不可逆转的形势。
高树德认为,城镇化、全球化和信息化给人们的生存带来便利,同时给作家也带来了“压迫”,尤其是市场化,一切以价格为衡量标准的市场化下,作家的境遇受到了无情的压迫,作家的生存状态受到了严重的“价格”挤压。才质不错的人,有文学天赋的“布衣”草根,如果在已往的年代传统的社会,通过辛勤的努力,还可能谋一升半斗稻粮,在如今已不大可能了。一篇文章,一本书成就一个人,成为天下人皆闻的作家,待遇优渥,那是几十年前上百年前的事了。文学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律,有天赋而没有板凳坐十年二十年的冷,要想暴得大名,要想有佳作闻世,那只能是空想而已。而市场又有自己的铁律,那就是求新求异求佳作。疲于奔命迎合市场,与读者过招拆招,浪费光阴和才华也许得来的是读者眼中的鸡肋。一将功成万骨枯,一作名世万滴血。又况且,作品真的优秀作品,若中国的《红楼梦》,国外的《红与黑》,被读者认可,已是作家故去多年后的事情了。
写作的规律,市场的规律乍看难以相容,但究其实质,规律也是有其相互兼容、彼此承认、相互尊重的一面。因此尊重规律,无论是写作还是市场,都是一个作家应该信守的。以创作的量取胜固然重要,但是读者和市场看重的是作品的质。乾隆皇帝以历史或现实的眼光来看均是成功人士,他一生创作的诗歌,其数量超越了诗歌史上创作量最大的诗人陆游。然而非专业研究者,一般读者有谁能背出乾隆皇帝三首五首诗呢?
采访中高树德一再强调,他并不是否定多产一定没有优秀作品,并不肯定量少就能有佳作。写作有写作的规律,就一般作家而言,也有禀赋超群的作家,才情并盛汗牛充栋的作品古代和当下都有。但他又说,作家和演员不一样,同样是创作,作家的创作在暗处,演员的创作在显处,作家不能学演员,一流的作家演戏,演不过末流的演员,为艺之道不同,况且作家内存不仅仅是高超的技艺,更重要的是他的灵魂。
冷板凳上的禅定之功,是写作这门道内的硬功夫。
面对纷纭世象,作家还是要用生命的真诚去写作。
作家是精神食粮的生产者,灵魂工程师,这些称谓和称谓下的内涵,在当下看来似乎背时陈腐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需求,只要揖别猿,人类还将继续存在,并且要存在的好一些,文学是不能缺席的。在信息繁盛令人炫目的当下,在价值观紊乱令人无所适从的当下,作家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,作品显得不那么需要了。作家不能先知,作家甚至不能已知,随便一个人,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在互联网上就可以知道。没有一个时代,在过去的几千年间有如此敏捷而不费吹灰之力得到答案的。作为灵魂工程师的作家,民众的先生,显现得十分低能。网络时代的到来,民众的文学素养,哲学素养,宗教素养,文化素养,前所未有的提高和普及。
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人,可以就文化侃侃而谈,谈得头头是道,而他或她从事的职业几乎没什么文化含量。一个蹬三轮的,被称为引车贩浆者,谈起宗教,譬如佛教,登堂入室,常常令人咋舌。民众的求知和接受教育不再是学校的讲堂,不再是纸质的媒介,作家和作家的作品,仅仅是其接受信息的一个很细的管道。民众素养提高,审美审丑的能力普及而提高几乎是匪夷所思。
铺天盖地的媒介,需要无穷数的作品,消费时代的到来,粗制滥造的作品在赶期赶档。若名著影视作品,一再翻拍炒冷饭,本钱再大,砸的票子再多,浑身解数使尽也难使冷饭变热变香。娱乐消解了庄严,消费成了一次性的快餐,民众大脑充塞满了垃圾。餐桌上的苏丹红、三聚氰胺、地沟油、固然是图财害命。精神餐桌上的苏丹红、三聚氰胺、地沟油,其图财害命的程度更甚。
高树德谈到,文学由传统的显性存在,到目前卑微到作品作家的边缘化,似乎社会不需要了。其实,只要人类要生存,要发展,要完善自我。优秀的作家,优秀的作品,比以往的社会和时代更需要。
作家是精神产品的创造者,是精神世界的殉道者。孤独和寂寞,灵魂中的厮杀毁灭,甚至形诸于形体。在艺术的行道中作家的自杀率要远远高于普通人,要高于其他艺术门类。这个在文学史上虽未引起重视和关注,但确实令人扼腕。在这个讲究成本,讲究价格的社会上,一个优秀的作家担负人类赎罪般的孽债,付出的代价甚或是生命的全体。
一个严肃的作家,一个优秀的作家,是用灵魂之善对抗世俗之恶,肩起重闸,让光明之希冀射照到读者的心田,为人世间做着牺牲。
高树德不是悲情主义者,甚至有点爱幻想的乐观。别的东西可以娱乐甚至游戏,写到白纸上的文学作品,不可掉以轻心。古人敬惜字纸,这个春天的上午,艳阳高照,春风和煦,被采访的高树德,几乎是敬惜文字了。他说敬畏出手的文字,就是恭敬读者,恭敬读者就是自尊。(本报记者 刘晚)
【责任编辑: 高卓然】

责任编辑:临汾新闻网编辑